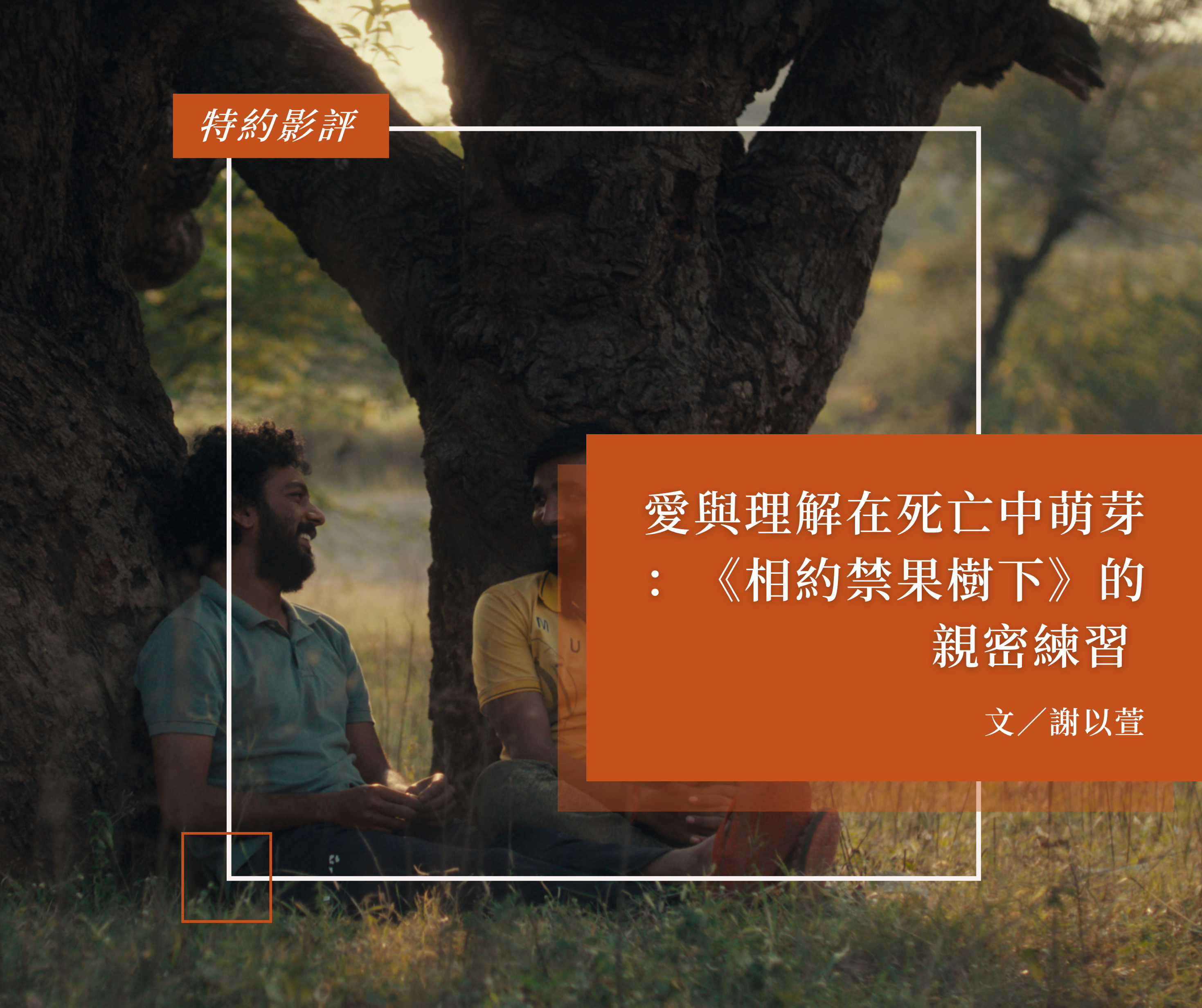文/謝以萱
死亡從來不是終點,而是故事的起點,是經驗真實人生的前奏。導演洛汗.帕舒拉姆.卡努列(Rohan Parashuram Kanawade)的首部劇情長片《相約禁果樹下》是首部獲得日舞影展世界電影評審團大獎的馬拉提語(Marathi)電影,故事的起始與導演意圖述說這故事的起心動念,正是源自他自身經歷父親死亡的經驗。
電影從主角阿南德 (Anand)父親的死訊展開,他從孟買返回故鄉,參加為期十日的傳統喪禮。阿南德是一位年過三十、未婚的男子,這讓他的存在在家族喪禮中的角色顯得相當曖昧,在那「男大當婚,女大當嫁」的傳統農業社會價值中,未婚也無對象的阿南德與親戚之間存在一種難以明說的緊張關係,而親戚們對他的批評則多半包裹在「關心」的名義下。然而,真正令親戚們不安的,是他對主流價值的「軟性抗拒」。電影並沒有聲嘶力竭的對抗,也沒有火爆直接的衝突場景,導演選擇將複雜的情感導入徐緩與延時的敘事節奏裡。
電影的多數鏡頭是少言、沈靜的,但並非靜默無聲;相反地,導演花了相當大的心力透過音畫語言,特別是聲音設計,打造出人物身處印度農村、受限於傳統社會價值,同時深陷至親逝世的哀悼與壓抑心境。那是一種透過多層次的電影語言,感官式呈現出的人物生命風景。
創作團隊實地錄製了 600 多個小時的自然環境音素材,包括家畜聲雞鳴鳥叫、風吹雨落、村民聲響;電影不採取單一的配樂,取而代之的乃是精心堆砌起的環境音牆,讓觀眾身歷其境地進入農村的生活節奏、進入人物生命中那段體感時間漫長的哀悼時刻。它不急躁、不喧嘩,它是人物內在狀態的投影,重建的日常音景仿若也成為敘事的另一位主角。
阿南德的哀愁與抑鬱,並非只來自摯愛的父親死亡。疊加在對死亡的哀傷之上的,還有傳統社會對其的束縛。他在村裡與舊識 巴利亞 (Balya)相逢,兩人發展出一段曖昧而親密的情誼。在人際關係過於緊密的農村社會裡,阿南德的悲傷與抑鬱需要空間與時間承接,巴利亞和他的相處,提供了溫柔的喘息機會——兩人貼身摩托車雙載馳騁在人煙稀少的山間小路、在風騷動枝葉的樹蔭下搓揉彼此的髮絲;每一次肌膚相擁與鬍髭相觸,不僅是同性戀情的展現,也更關乎身處在悲傷之中的人們,如何重新賦予生命自由,肯認自我、感知愛與歸屬的可能。
當父親的喪葬儀式逐漸步入尾聲,阿南德提出要帶巴利亞回到孟買工作時,親戚對其不婚的質疑再度浮上檯面。阿南德的母親作為最了解兒子的人,則巧妙地以他曾在感情中受創為他的不婚圓場。出身低微的母親,如今成為寡婦後在家族中更沒有地位,她為阿南德編織的小謊,可說是同樣身處父權家族長結構邊陲的母子兩人,攜手共同編撰的生存策略;阿南德則擔憂自己的「踰矩」將會為母親帶來麻煩,特別是遭受親友的閒言閒語。那幕母子倆在天臺上的對話場景動人地呈現親情的力量,其實彼此擔憂的不是其他,而單純只求對方能否過得順心自由不受傷害。
《相約禁果樹下》是一部關於自由與愛的電影。電影探問的是如何在社會規範的限制下撐出空間,為身心靈找到得以自由安放的可能;當衝突發生時,能如何理解與和解?阿南德的憂愁,泰半也來自父親驟然而逝後的空缺,那空缺乃是他的酷兒身份尚未有機會向父親表述的遺憾,他在意的,不是其他外人對他的看法,乃是父親生前是如何理解他的不婚。然而,生死已兩界。
導演相當細膩地透過幾個場景來呈現生死兩界後的連結,例如神婆透過米占斷言父親轉世為鳥,而阿南德在林中漫步聽聞鳥鳴後,身心感到撫慰;以及,喪葬儀式來到最後一階段,因儀式剃髮後的阿南德獨自坐在廟裡睡去,半夢半醒間,他看見父親站在哈努曼神廟裡對他微笑,父子倆相擁,一個了然於心,無須言語的、深沈的擁抱,阿南德趴在父親的肩膀上,流露出安穩的神情。
《相約禁果樹下》不僅是一部優雅動人的當代酷兒電影,也是細膩勾勒出鑲嵌在生活各層面的印度家庭故事。導演曾說他拍電影是希望將「生活帶上大銀幕」,他指的「生活」不僅僅是寫實的經驗,而更是提供人們一種感受生活與想像現實的途徑,當我們伴隨著電影中的人物一同經驗的時候,對於不同於己的人事物便多了些理解的機會。即使那仙人掌果本身帶刺,但在每一顆帶刺的果實之中那多汁甜美的內裡,有著一個差異得以共存的世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