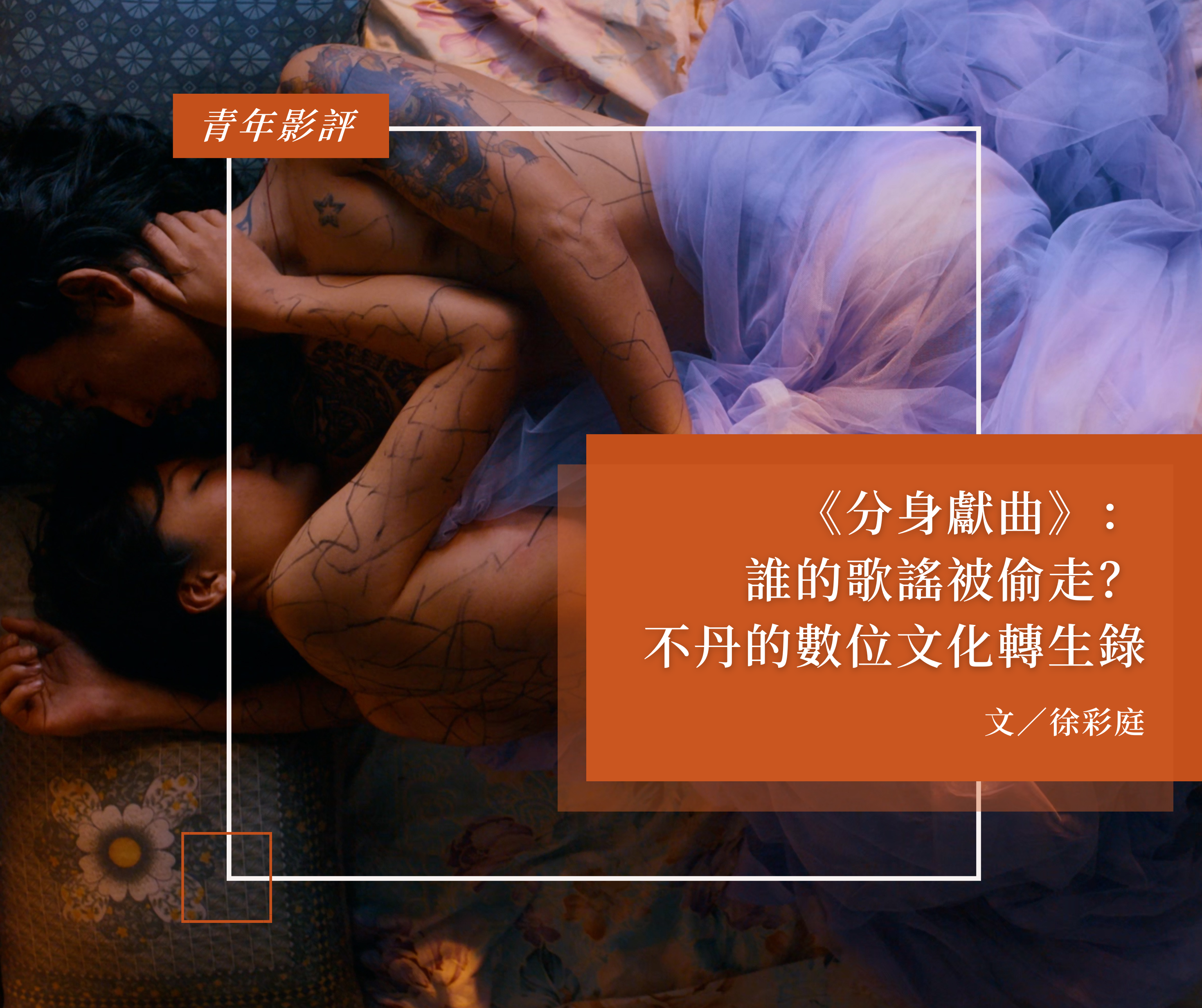文 / 徐彩庭
妮瑪在不丹的首都辛布擔任學校老師,文靜規矩的她卻被指認為一部色情短片的主角。從校長、家長到男友,無人相信她的清白,只因片中女子有著與她一樣的臉龐。無故丟了工作,又被另一半冷眼相待,妮瑪決心找出影片真正的女主角以挽回名譽。片中的隱藏線索將她引導至不丹南方小鎮,她很快發現自己的神秘分身是一位名為梅托的女子。然而,無論是梅托的前男友、家人、上司或朋友,無人知曉她的下落。謎題尚未解開,妮瑪卻已牽扯進更多神秘事件:關於被都市人偷走的傳統歌謠、林間的儀式,還有虛實交錯的夢境⋯⋯
座落於喜馬拉雅山脈上的不丹,總人口不超過八十萬,直到 1974 年才開放外國旅客入境,超過四分之三人口信奉藏傳佛教。濃厚的宗教色彩與與世隔絕的神秘氛圍,使不丹被譽為「最後的香格里拉」,同時也因政府對「國民幸福指數」(Gross National Happiness)的重視而獲得「世界最幸福國度」的美稱。然而,外人眼中如仙境般的國家,其實正面臨現代化的巨大衝擊。
本片導演 Dechen Roder 在《Variety》的報導中指出,不丹社會一夕之間從口述傳統跨入由影像與視覺主導的文化:「現代化的速度快到嚇人。」《分身獻曲》透過兩位女子的故事、反覆閃現的歌謠與儀式,呈現不丹傳統文化在二十一世紀變形轉生的現象,並藉「分身」概念探索在這股浪潮中,關於身份選擇與生命意義的問題。
《分身獻曲》的靈感源自兩個真實事件:一是導演的朋友經歷妮瑪的窘境,驚恐發現自己出現在外流的色情影片中;其二是導演聽聞一則故事,講述偏鄉居民抱怨首都辛布偷走了他們神聖的歌曲,將歌謠從原本的文化脈絡剝除,改編並隨意在電視與收音機上播放。兩件事的核心皆指向同一困境:數位時代的傳播力讓原屬私領域的秘密事物被「偷走」、任意流傳,受害者卻無從追究責任。而當這些事物在網路上、地理空間中或文化脈絡上越走越遠時,便如同經歷了投胎轉世——面貌如舊,本質卻已全然改變。
妮瑪與梅托的關係彷彿一首「出走」的歌謠,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臉孔,卻實則是兩個不同的人:妮瑪是留學紐約的知識分子,在首都過著平淡而疏離的生活;梅托來自偏遠山區,天真爛漫,嚮往當歌手與前往美國,卻因誤信他人而遭遇巨變。飾演女主角的 Tandin Bidha 分享,在不丹有種說法:人去了美國便會改頭換面,變成另一個人;若有人突然消失,他們會說那人「去了美國」。梅托失蹤前向朋友借錢,聲稱要赴美,也呼應妮瑪留美返鄉的背景——兩人彷彿真能串連成某種前世與今生。
不過,梅托的離開與妮瑪的到來,並不預示傳統文化終將被現代浪潮取代的結論。直到故事尾聲,妮瑪費盡心思,甚至深入險境,企圖尋找拍攝與散播色情影片的真凶,卻發現意外真相。最終謎底揭曉,兩人身份再次流轉,畫出命運輪迴的圓圈。
在電影與文學中,「分身」經常象徵某種惡兆。比方說,動畫電影《藍色恐懼》中,主角的人生因分身的出現而陷入混亂,直到分身毀滅才回歸正軌。《分身獻曲》中的梅托一開始也確實扮演令妮瑪陷入困境的反派,妮瑪尋找她的動機是為了「奪回原本的人生」。然而,梅托的前男友坦丁曾反問:「為什麼要奪回原本的人生?」彷彿在質問,妮瑪原本的生活到底哪裡更值得?哪裡比梅托的更好?坦丁的提問與這趟旅程,讓妮瑪得以從距離中重新審視過往,最終選擇放下執著的身分認同,與自己另一種「可能的面貌」和諧共存。
擁有梅托的名字與妮瑪的本質,電影終幕時出現在鏡頭中的這名女子,既繼承傳統,也堅定展現現代女性的精神:勇敢捍衛自己的權益。《分身獻曲》珍視傳統的神聖與獨特性,亦大膽突破——Tandin Bidha 表示,一人分飾兩角並非本片最大挑戰,真正的難題是接吻:她與坦丁的親吻,是不丹影視史上第一場吻戲,在傳統的不丹社會裡,她甚至不能確定能否繼續演戲!好在大眾接受了藝術的詮釋。
《分身獻曲》以古老的轉世與分身傳說回應數位化帶來的衝擊,傳統與前衛、民謠與電音、都市與鄉村等看似二元的符號,從天秤兩端被釋放,等待彎折、疊合,重新融合成不丹更加自在而堅定的未來樣貌。